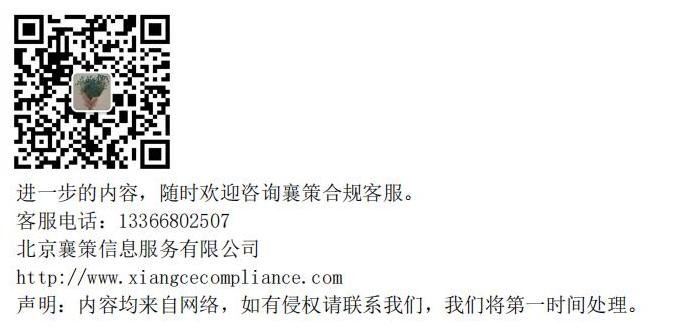境外收入结构化安排
录入编辑:襄策合规 | 发布时间:2025-09-09在跨境财富管理中,境外收入的结构化安排长期以来是一种常见的筹划手段,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复杂的法律与金融工具,将本应直接归属于个人或企业的境外所得,转化为形式上不属于申报主体的收入,从而延缓或减少纳税义务。这类安排在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时代确实为高净值人士和跨国企业提供了操作空间,但在共同申报准则(CRS)与全球税收透明化趋势下,原有的结构化手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常见的结构化安排之一是通过设立离岸公司作为持股平台。个人或企业通过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注册公司,以公司名义持有境外投资或银行账户,从而使相关收益在账面上表现为“公司所得”,而非个人所得。这种安排在境外司法管辖区往往具有低税甚至零税的环境,配合缺乏自动信息交换的制度,曾被广泛用于资本外逃和税收递延。然而,随着CRS的逐步覆盖,这类离岸公司一旦被认定为“被动非金融实体”,金融机构就必须穿透披露其最终受益人,中国居民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将直接传递回国,隐匿的效果随之削弱。
另一类典型做法是通过信托、基金或保险工具实现收入再包装。例如,将股息分红、利息收入注入信托账户,再以受益分配的方式进行发放,表面上受益人身份被信托架构掩盖,实际则企图延缓申报义务;又如利用投资连结保险,将投资收益与保险合同绑定,试图规避所得性质的认定。这些安排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延迟效果,但在CRS的尽职调查和穿透申报机制下,信托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身份均可能被披露,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和领取金额同样在交换范围内,换言之,金融工具的包装已不足以完全隔离税务机关的视线。
部分跨国企业则采用利润转移与定价安排来实现结构化。通过在低税司法区设立关联公司,将知识产权、融资功能或采购环节外包给境外子公司,以此将利润在账面上转移出高税地区。虽然这种操作涉及转让定价规则而非CRS直接覆盖的范围,但在全球反避税(BEPS)行动计划和中国税务机关不断强化的关联交易管理下,这类安排同样面临日益严厉的合规压力。中国近年来多次发布典型案例,表明对于通过虚构成本、过度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跨境资金循环等方式实现结构化的企业,将进行追缴和处罚。
在现实操作中,境外收入的结构化安排并非完全不可行,但其合规空间越来越依赖于合法筹划而非制度漏洞。以双边税收协定为例,如果中国居民通过境外投资取得股息或利息,可以根据协定享受预提税率下调的优惠,进而降低实际税负;又如在境外已缴税款的情形下,通过境外税收抵免机制抵扣国内应纳税额,也是一种合规的结构化方式。这些合法路径与“隐匿性”安排的差别在于,它们不依赖信息不透明,而是基于税收规则的合理运用。
在CRS环境下继续依赖传统结构化安排的风险不容忽视。已有案例显示,中国居民在境外通过离岸公司投资证券市场,试图避免直接暴露身份,但在尽职调查环节被银行识别为最终受益人,相关信息回传后触发了补税与罚款程序。也有家庭通过信托代持境外不动产,但因受益人未如实申报分配收益,最终被税务机关要求追溯申报。这些案例表明,结构化安排一旦与逃避申报挂钩,不仅会失去筹划意义,还可能演变为合规风险。
未来境外收入的结构化安排将更加依赖透明合规的制度化手段,而不是灰色操作空间。一方面,OECD和各国税务机关正在不断完善穿透机制,例如拟将不动产纳入信息交换范围,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纳入申报义务,意味着任何形式的隐匿性资产最终都有可能被追踪。另一方面,中国税务机关通过大数据分析、跨境支付监控和外汇申报制度,已经具备多维度识别境外收入的能力,这进一步压缩了灰色结构化的空间。在这一环境下,纳税人若希望通过境外收入安排实现税负优化,应更多依赖税收协定、跨境抵免、合理的公司架构设计,而不是依赖不透明的工具。
总的来看,境外收入的结构化安排正处于从“隐匿避税”向“合规筹划”的转型期。传统意义上依赖离岸公司、信托和保险的做法,已不再能够保证信息安全与税收递延,而合法利用国际税收规则实现优化,才是可持续的路径。对于中国的高净值人士和跨国企业而言,关键在于认清合规与风险的边界,调整思维,从“如何隐藏”转向“如何合规且高效”。这不仅有助于降低长期税务风险,也有助于在全球化竞争中建立更加稳健的财富与资本管理体系。